 中传云资讯系统
中传云资讯系统评论 | 揭示《朱子语类》的文体内涵和价值
刘振英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与我商量要写《朱子语类》,他硕士论文就是以朱子为题,继续研究也很自然。但《朱子语类》收录朱熹一万四千多条语录,字约二百三十万,如振英所言,包括对天地、鬼神之理的探索;对性理、学行的审问和深研;对儒家核心典籍的诠释;对学术异端的论争、对道学传承和正统的捍卫;对历代卓越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讲述,对社会兴衰治乱规律的总结。我感到有相当难度,心里颇犹疑。后与振英聊,发现他崇敬朱熹,《朱子语类》已经读得很熟,增强了我的信心。
朱熹是宋代著名理学家,历元明清,他的学术思想一直是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自宋代以后,儒学主要是通过朱熹而形成对于中国影响的。正因为如此,研究朱熹的成果甚多,哲学、美学、语言学都已经研究十分深入。朱熹也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他为官十余年,而讲学却长达半个世纪。乾道五年(1169),朱熹返里守丧期间,创办了寒泉精舍,讲学八年之久。淳熙七年(1180)朱熹知南康军,修复白鹿洞书院,并主持、主讲书院。淳熙九年(1182),迁台州主管崇道观,于武夷山建武夷精舍,在此讲学亦达七年之多。绍熙四年(1193),朱熹离潭州之任回归故里,又建竹林精舍,成为他晚年居家讲学的学院。所以如果要为朱熹正名,他名副其实就是个老师。
老师的天职是授课,但朱子讲课的方式与今绝不相同。今日高校教师讲课,本科基本是满堂灌,教师讲完就走,很少与学生交流。研究生尚好,但据我所知,硕士也是以导师讲课为主,博士或许研讨较多。我一直认为,文史的教学,应以读书为主,辅之以教学辅导。而今天恰恰反而行之,孰对孰错,没人检讨。书院教学,就是以读书为主,然后师生互相研讨,老师的作用就是解惑答疑,于是有了《朱子语类》之语体。这个语体,不同于《国语》的语体,与《论语》大体相似,是一种独立的语体。它类似教材,又不同于教材。它有问有答,有来有往,形同对话;可它又不同于对话,虽然有问有答,但讲话主体却是老师。所以语非七嘴八舌的杂语,话非对等的对话。《朱子语类》的语体是建于宋代书院体制之上的讲授体,是发生在师生之间的一种讲授艺术。朱熹不仅是位教育家,还是一位文学家,其诗文在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他与学生学术交流,或论道,或讲经,或讲史,很重章法,颇具语言艺术,体现了朱熹文章学的深厚功力。研究朱熹的论著多矣,很少有人研究朱熹作为文学家与学生研读讲授的语言艺术;研究文体的论著亦多矣,也未见研究教育家创造的一种文体——极为特殊的讲授体。总之,立足文章学研究《朱子语类》,揭示其文体内涵和价值,振英论文的学术意义也许正在于此。
论文写作难度较大,过程并不顺利。南开大学教授查洪德研究元代文学,于理学颇有心得,我请他和我一起辅导振英的论文。我、洪德和振英几乎是在不断讨论中,理清思路的。论文取得的收获,窃以为主要在于扣准文章学,首次研究并揭示出《朱子语类》作为授课语体的语言艺术。
首先是讲述语体的研究。为了总结社会兴衰和治乱规律,朱熹常与学生讲述历史、评论当代人物事件,形成了《朱子语类》的讲述艺术。振英的论文着眼于《朱子语类》人物与事件的叙述,总结其讲述人物的语言艺术:既注重人物之间的映衬关系,又注重人物学术灵魂的捕捉,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立言立心。而朱熹讲述事件,注重情节的上下相接和“因果互生”,按照讲述目的来安排讲述情节的先后,讲述中的“插叙”“倒叙”“补叙”都能使事件讲述别开生面。
其次是讲解语体艺术的研究。朱熹与学生研讨的重要内容仍是儒家经典,即《四书》《五经》。在讲解儒家经典之中,亦阐述朱子理学的天地、性理之学。振英论文亦以文章学为视点,把握朱熹讲解四书五经的语言艺术,从体裁论、体要论、体貌论等几个方面分析朱熹的讲解过程,剖析理学思维与讲解方法、讲解篇体之间的内在联系。结合朱子的理学思维解析其解经的文章学内涵,应是论文的难点,总体看,此部分取得的收获也最大,在研究朱熹的论著中有其独特的价值。
第三是论辨语体艺术研究。论文把朱熹在课堂上梳理学术分歧,明辨是非,判断价值,构建道统的内容,归为论辨艺术。振英具体研究了朱熹辨析问题时,论辨之气势、论辨之节奏、论辨之语言和论辨之方法。细致到论辩的起势、蓄势、收势,虚字、文眼,造语、口语。振英论文的第一稿就是把《朱子语类》作为语料来研究的,虽然后来改变了路数,但第一稿所下的功夫,在此一部分充分展现出来。
作者总自谦不如别人聪明,果真如此,此论文就是笨人读书研究的成果。肯于下笨功夫,爬梳文献,吃透内容,理出思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研究清楚,写出自己的心得,由此而推进些许朱熹文章学的研究,这也许正是笨的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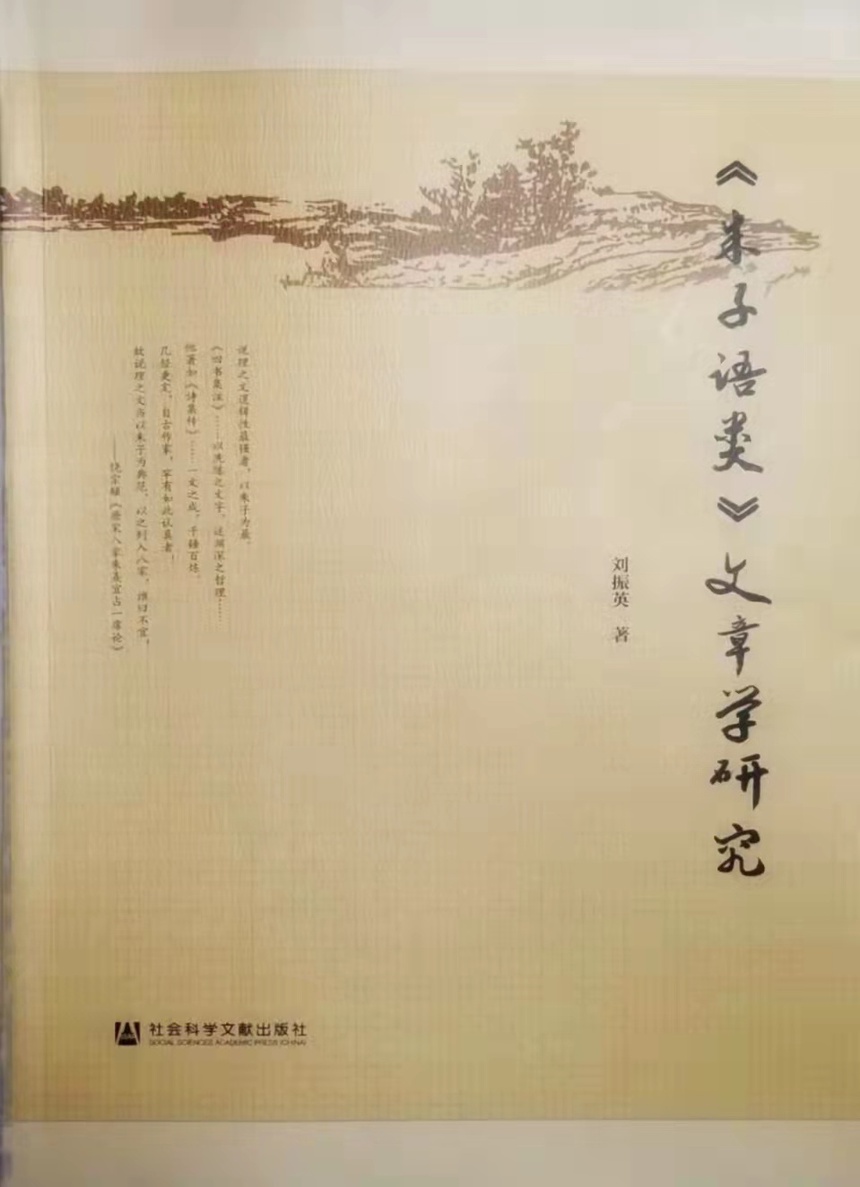
(本文为《<朱子语类>文章学研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