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传云资讯系统
中传云资讯系统南方观察 | 徐畅、宫敏捷:爱与隐秘——《鱼处于陆》访谈录
近日,青年小说家徐畅的小说集《鱼处于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小说集由九篇小说组成,从故事线索上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成长,以及对个人精神的探索。从结构上来说,短篇集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辑有《鱼处于陆》《母亲》两篇,主题侧重于家庭与时代;第二辑有《良宵》《苍白的心》《山体环绕》《醒来》四篇,主题围绕“得不到的爱”,故事中人物困在爱的边缘,不得不转向内心生活;第三辑有《窒息》《狐》《安静》三篇,描写了三个不同的人物,一个是执着于情欲的小镇女性、一个是回乡解开弟弟谜团的青年、一个是逐渐丧失听觉的诗人。作者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从他者身上寻找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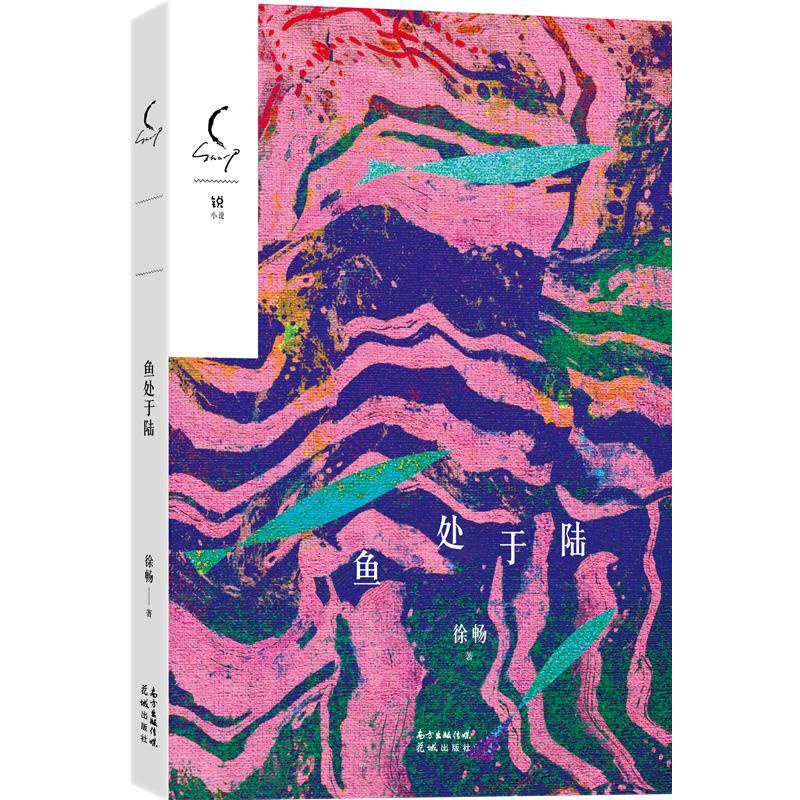
2022年5月27日,藉由该书的出版,青年小说家、评论家宫敏捷,与徐畅围绕着《鱼处于陆》及徐畅小说的创作本身,展开了深入访谈。访谈主题为“温故那些爱与隐秘”。
以下为文字实录——
宫敏捷(以下简称宫):徐畅老师,首先得恭喜你的小说集《鱼处于陆》于疫情之下,由花城出版社顺利出版。这本书是你的第一本小说集,是你三十余年生命历程里,第一次用文学的方式,具体来说是以虚构的方式,将思想的结晶和盘托出给大家看。从你的后记所明示的内容,以及一篇篇充满探索精神的小说本身,我们都可以看来出这一点。所以我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这本书的出版,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徐畅(以下简称徐):这部小说集的出版给我很大的写作信心。我想对于任何一个写作者来说,自己的作品能够出版,都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这部作品集于我,如同小时候期末考试结束后意外得到了一张奖状。这些作品大概描摹出一个人从童年、少年到青年以来的人生境遇。对我来说,小说集的出版是一个节点,也是新的起点。我更愿意在此基础上,做更多的摸索和尝试。
宫:第二个问题,其实是前一个问题的延伸。那就是你为什么要在个人简介里,特别强调自己“曾在喜马拉雅山脉游历”;如果你真的不避讳的话,我还想深入了解一下,你后记里写到的长达十年之久的“寄住生活”,会不会给你的心理带来某种创伤?
徐: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成为现在的模样,一部分原因是自己的学识,还有一部分就是自身的经历。我在简介中并没有刻意去强调这两段人生经历,只是觉得这些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个人。不过呢,我也觉得人是很奇怪的,当我们回顾过往时,想要提到的就是那些真的改变了自己的事物。不管这样的事物,是好还是坏。
“喜马拉雅游历”,只是一次长时间的旅行。那时候在读书,也没有多少钱,就背着帐篷在藏区待了一段时间。可能徒步过程中遇到的很多意外、一些奇特的人,慢慢影响了我对人生的态度。我以后应该不会再提起这段经历,因为我觉得有的读书人并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但是在精神的探索上却走到了世界尽头。
“寄住生活”,是人生的无奈,也是少年时候要面临的最大困境。那时,我总是很悲观,一想到还有好几年才能读完中学,就唉声叹气。因为先是住在爷爷家,后又住在舅舅家,内心自然就会变得敏感。别人随便的一句话,到我这里就会出现复杂的意思。有时,也会受不了。时间长了,在生活中就经常去“逃避”人和事。那时候喜欢读书,估计跟这种心态也有关。
但是我并没有要去“自怜”,我觉得不管人生到了何种处境,都要往有希望的地方去看。对一个没有退路的人而言,前进应该是唯一的方式。这应该就是少年时有价值的感悟吧。
宫:我们可以把《鱼处于陆》当作是你对自己的一次精神解构吗?还谈不上和解,但你想把一些“隐秘”的东西,加一层“虚构”的外衣,展示给自己看,毕竟,你把这次分享的主题定为:温故那些爱与隐秘,一定是有其深意的。
徐:是不是精神解构,我不知道。应该不算。毕竟还没有一个成熟的精神状态出现。我的写作,是倾向于忠实自我的。所以在写作中,到处都是自己的影子。甚至有的时候,那些虚构的细节,别人看来认为是真实的。我暗想,这可能也是一个优势。其实任何一个写作者都是知道的,我们写作就像织毛衣,那些虚构的细节在笔下拼接、试错、重组,而所谓的“事实”,只是那一张毛衣图案。
将主题定为爱与隐秘。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小说中写了很多与爱有关的故事,另一方面是在主题上的表达相对隐秘。比如《苍白的心》这篇像是在写一个三角恋,但是它隐藏的主题完全不是在情感上面。
宫:虽然你说,九篇小说的脉络连起来,“从成长轨迹上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成长,以及对个人精神的探索”,但这毕竟是虚构的艺术作品。你所表达的,我们不一定会相信,尤其那些故事,他们看起来很真实,但我知道,它们的真实是逻辑支撑上的真实,而非故事本身。但情感,你通过虚构传达的情感,这个情感,不管是你作为作家个人的,还小说人物的,都是真真切切的,也是可知可感的。海明威说:“作家的工作是告诉人们真理。他忠于真理的标准应当达到这样的高度:他根据自己经验创造出来的作品应当比任何实际事物更加真实。”你的这个小说集,能否用来佐证这句话?或者说,你的个人经历,与不同篇章里的小说人物,都有某种重合,当然,有时候是故事,有时候是情感?
徐:是啊。在小说里,当然是虚构最重要。我们读现代派作品,那种感觉就不是在讲故事,而是直接讲那些极端的感受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读那些作品,其实就是直面那些煎熬。
我自己写作的时候,其实也是想对某一个虚空进行表达,只是形式是故事、是人物、是细节。但是表达的效果是有好坏之分的。有的名作家利用现实题材才能表达得生动,而有些作家完全建立在想象中去表达则更加集中。就像《审判》和《动物庄园》不同的表现形式。
宫:从这个小说集来看,在将个人经历提炼成不同的小说方面,你做得非常好。这方面,可有一些独到的经验告诉我们?
徐:回忆。那应该就是回忆了。回忆是非常主观的,但是它确实有着“提炼”的作用。它会自行筛选那些看起来对自己影响很大的事情。虽然客观上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回忆的时候,就会有意去放大。我感觉这种放大和筛选,在一定程度上对写作是有帮助的。
不过这些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作者比较敏锐,而且知道哪些东西值得去写。
宫:《鱼处于陆》这一篇,写的是一个家庭的建立到破碎,同时也对应展示了那个时间段的历史变迁,以及人在其中精神的变化或异化。他们对自我的认识及对世界的理解,都带有明显的局限,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但他们对自己坚信不疑。人的坚持就在于此,崩溃也在于此。那个母亲,她只想办一所幼儿园;那个父亲,他只想教书,教语文。他们之间,是那个作为观察者的孩子,也是他们最深爱最看重的人,他逃无可逃。这会让我想起塞万提斯笔下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或者是那个悲情英雄西西弗斯。你在文中,用了大段的篇幅书写了时代本身,其深意就在于此还是其他?
徐:《鱼处于陆》这篇小说写得比较用力。就像您说的,小说的重点是在这位母亲身上。小说中通过“我”看电视的视角,侧面去写了很多城市里的现实变化。这里的时间变化其实是加速的。我也是有意这样去写。因为小说想写的其实是带有理性主义色彩的时代变迁与非理性的人之间巨大矛盾。渺小的个人站在巨大的浪潮面前,其实不堪一击的。但是人的价值,有时也体现在这一点,总是充满激情、充满对生活的渴望,虽然也知道自己的坚持是渺茫的,基本改变不了现状,但是就这么坚持过来了,人生也有了意义。
宫:《母亲》这篇小说里的母亲,与《鱼处于陆》里的母亲,至暗时刻,都喜欢喝醉自己,这一点很有意思。我想你在创作时,应该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但这不是我要问的问题。《母亲》这个小说,如果我们给它加一个副标题的话,叫《酒局》最为贴切了。它不像《鱼处于陆》,承载一些宏大的思想性的东西,但却表现了人性与人心,那些不被太阳照见的东西,都被“母亲”做一个局,全部拿出来暴晒。这两个小说,在你自己的区分里,属于“第一辑侧重于家庭与时代”。但我还关心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曾与广东作家陈再见对谈时,他曾主动聊起来过,那就是“带着恨意”写作。这个恨,我们可以具体一点说,它是针对一个地方的,也是针对一个群体的。你也会有这样的体验并促成了这样的表达吗?
徐:“带着恨意”写作,我不是很明白它的概念。我想,这个应该是基于人物的说法。人物带着恨意,那自然是可以的。在写作当中,不管多么强烈的情感,写作者应该是保持理性的。而且我觉得越是强烈的情感,越应该有所克制。我之前看到过,小津安二郎曾对笠智众说,你演父亲的时候,不用有过多的表情,你就把自己的脸当成一张纸。因为你传达的越多,观众接受的反而越少。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关于传达的教训。
宫:相对于前两个小说,从艺术上我更喜欢《良宵》,它更短小精悍,更有爆发力,或者说从表达上,更加精准。前两个小说相对来说,也不是说表达不精准,但还是“写意”了一点。这个小说的精准,指的是作家对人物情绪的精准把握与传递,里面喝啤酒比赛的场面也十分震撼人心,可以说,小说的创作就是基于这一点去虚构的,这也是你所说的“隐秘”的一部分吗?
徐:“喝啤酒比赛”那个细节,是我听来的。本来是一个比较好玩的故事。就是商场里举办活动,那个人酒量很大,赢了那个布娃娃。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常见到。但是放到小说中时,那里的描述确实让人有点情绪化。这也跟小说的表达有关。这个“隐秘”的一部分,是想说,自己所谓的爱在别人的爱面前,简直不值一提。在爱的面前,是不分阶层的。
宫:《山体环绕》里,看到其中一段:“那个时候,韩晴走上来突然问,你想过把你舅妈叫作妈妈吗?”我突然间觉得那个叫“李原”的男人就是作家本身,但作为同是写小说的人,我知道不是。我喜欢作家在小说里,跟自己开玩笑。这个个小说集里,还有哪些玩笑是你跟自己开的,我们却没办法看出来的?
徐:会有这样的情况。在写作当中,有时会跟自己开玩笑。小说里有许多这样的细节:里面的人物喜欢养蜗牛、总是做很长时间的梦、心理活动特别繁复等。写作的过程,是一个焦虑的过程。有这些细节,反而会觉得有趣一些。
宫:《山体环绕》里面,那种隐忍的无处安放的爱,很是迷惑人心,也是因为这一点,小说的张力才能保持始终。但我知道,你想表达更多东西,以至于看到最后,我对小说里套进去的那个彩色男人最后消失于无形的故事,印象更加深刻,这是这个小说的神来之笔。我们还能看出来,借用动漫化卡夫卡小说人物的方式,你其实套进去了更多的小故事。这个小说就不是始于爱又止于爱那么简单了。我们都知道,阅读卡夫卡与解构卡夫卡,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可否藉由你这个小说的创作,给我们好好谈谈?
徐:“彩色男人”背后有个挺悲伤的故事。我有一个同学在服装印染厂里工作,他负责染料的配置。他跟我讲,工作了一天下来,吐口水都是有颜色的。那时我就想,在现代工业的流水线上,要是一个人一下子消失了,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人物消失了,就像小说的主人公如果从困住他的爱中逃出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爱,有的时候反而是一种负担。这也是“隐秘”的一部分,但是很少有人愿意说出来。
前面讲过卡夫卡的小说,是直面人的困境的。我们刚开始读《审判》的时候,觉得一个人突然被带走了,这个事实似乎不太容易接受。但是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这种危机感一下子来到了我们的面前。愚钝的我们,是看到了现实才有这种感觉,而卡夫卡在一个相对平和的环境下,就有了这样的预感。这应该就是天才的感知力。
宫:《安静》在这个小说集里,显得有点 “另类”,不像《狐》或《苍白的心》那样,似乎总有作者的影子在里面晃荡。我是说,作为读者,我可以将这个小说,视为超越作者本身的一种存在。当然,这也是你想象力与创造力神奇体现。出于报复心理,孟夏勒死了医生的狗,就隔着一扇薄薄的门。这个画面极具张力也足够惊悚,这也是我觉得,这个小说可以超越作者而独立存在的地方。希望你能给我们详谈一下这个失聪者及其报复心理的创意写作如何得来的?
徐:这篇小说是在征得了一位朋友的同意后才发表的。里面失聪的经历,跟他有关。但是其他细节都是虚构的。我想写一种感官渐渐离开了人体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狗的情节,我没有刻意去写,只是觉得他要获得内心的平静,是可能会做一件残忍的事。这件事做完之后,他就真的接受了这个事实。
宫:你的小说文本,并不变化多端,但仍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优秀的小说家,有时候也是文体家。海明威说:“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他应该永远尝试去做那些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他人没有做成的事。这样他就有幸会获得成功。”在我理解里,海明威所指的“探索”,除了主题,也有文体方面的尝试。加之你的身份不仅仅是小说家,你同时还是一个专业编辑,可以说是“阅文无数”,海明威说的这种“探索”,你是天性使然,还是有主观能动性在里面,至少是带着使命感?
徐:我自己的写作,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焦虑。就是担心自己会越写越差,或者没有东西可以写。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您说的“探索”确实是能让人感觉到安心。有了探索精神,就可以写出更多的作品,可以尝试更多的主题。
我之前觉得有一个故事,应该放一放,想好了再去写,没有想好就不去写。这就导致写作的数量很低。估计这跟我当编辑也有关系。后来我看到有人说,对于青年作者而言,创作冲动比故事和主题更重要。因为这种冲动是一闪而过的,如果错过了,后面可能很难再进入这样的状态。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有道理。
宫:其实,我对徐老师的阅读,不仅仅是《鱼处于陆》本身,我们认识已经很有一段日子了,我还通过其他方式,阅读过你更多的小说。从而了解到,你的创作也是一个不断学习与实践的过程。我们能从你的文字里,看到一些大师的影子,比如上面聊到的卡夫卡,还有福楼拜、川端康成、鲁迅等。让你对日常的观察与描述,具有了诗意和深意,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这是两个问题:其一:还有哪些作家,你对他的阅读让你的写作受益匪浅?其二:作家写过去的时光,因为自带距离,就有了足够的客观,而距离与时间本身,就意味着洗礼与提炼。我们的平实书写也就具有了艺术的色彩;而表达和书写当下,稍不注意文字就会失控,变得冗长而毫无意义,主题本身也是这样。相对来说,你在《鱼处于陆》这个集子里,是做得非常好的。你的这种分寸感是怎么做到的?
徐:要列表的话,那肯定可以写出很多。托尔斯泰、契诃夫、库切、纳博科夫、福克纳、帕慕克、卡佛、托宾、巴别尔、鲁迅、周作人等。分寸感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可能这跟语言风格有关系。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是写短小说。我写了三十多篇短小说,后来才开始写中短篇小说。所以在后面的写作中,我会倾向于简洁。不管在表达和描述上面,都会相对集中。我们看巴别尔的小说,我们不会觉得语言是简洁的,但是我们说他的主题是集中的,甚至是尖锐的。
宫:《山体环绕》与《醒来》,在故事设计方面,或者说情节推进方面,有些相似的地方;前者是电脑里隐藏在压缩包里的照片,后者是塑料箱和日记本,透露了内心的秘密也抖开了过去的时光,人物的关系也就发生了变化。前者里,刘菲说:“我们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吧。”后者里,“他看到小钰发来的信息: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我想,这里面,你是否在将同一种“隐秘”情绪,用不同的故事去调节?
徐:嗯。我觉得同一个情节,过了几年之后再去写,里面的意味也发生了变化。写作里面有个说法是“重复”。就是同一件事,重复几次去写,里面的意思会有所不同。但是我这里并不是有意如此,更多是无意识中写到了相似的情节。这两篇小说毕竟隔了差不多五年的时间。
宫:《醒来》与《狐》中,都有一个“外婆家的圆圆。”从故事设计上,这是同一个人物不同时间段的生活遭遇吗?
徐:应该不是的。跟上一个问题类似。
宫:纵观这个小说里,几乎每一篇里,不管故事和主题如何,也不管人物的身份设置如何定位。在叙事过程中,我发现人物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人生与人性的思考,所以就不用一一举列了。如果要给这个小说集,提炼一个叙事主题的话,加上着重号的几个字就是。所以我想问的是,在你创作过程中,这是出于主题提炼及人物塑造的需要,还是你作为小说家的个人表达需要?比如像《窒息》里的这些话语:“她愿意牺牲自己,让人类变得善良。但在她等待就义的时刻,走上来的却是李瞳,李瞳浑身鲜血,滑在她脚下。麦安跟在身后,抱着钢刀两眼通红,他又在追问,是不是还有别人?是不是?现在她猛然明白,疯狂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她知道她能做的不是去拯救,而是尽快醒来。”
徐:我觉得人物塑造、个人表达都是有的。您列举的《窒息》里的片段,更多是人物塑造。如果作者来表达的话,肯定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和口吻。有些作品会通过人物之口,来表达作者本人的意思。在我的小说里,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但只是极少数。而且要在符合人物身份的前提之下。比如《鱼处于陆》里那个父亲说的一些话。
宫:你的人物还喜欢做梦,这也很有意思。
徐:是啊。谢谢您读这么仔细。我经常写梦境,其实是喜欢描写梦境时的那种缥缈又带着情绪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其他方面好像是遇不到的。而且梦里确实可以写到一些隐藏的真实。可能在现实中,要交代很多细节和对话,但是在梦境中,一个形象就够了。
宫:我很喜欢你这样的叙事表达方式,在我的理解里,你是在像沙漏一样的写作。沙漏的两端都是一样,但一边充盈,一边宽泛。砂砾往那一边流动——流动的过程,就是叙事推进的过程——其结果都是一样的。这让你的文本具有了清晰可辨的二元性。“沙子”(文字)的流动缓慢而持续,同时也是一个不断泄露与堆积的结果:充盈的一边,变得宽泛,宽泛的一边又变得充盈。他们不是简单的互为因果,而是相互支撑,在结构稳固的同时,小说的叙事也达到了最好的状态。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同时,我也希望在你未来的创作中,能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尝试与惊喜。

徐畅简介:生于1990年,青年小说家,江苏人。曾在喜马拉雅山脉游历,现居上海,《上海文学》编辑。获第三届“90后创意小说大赛”冠军,作品发表于《收获》《上海文学》《江南》《文艺报》等。

宫敏捷简介:青年小说家,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籍贵州威宁,现居深圳。中短篇小说发表于《上海文学》《长城》《广西文学》《湖南文学》《广州文艺》《山西文学》《南方文学》等刊。部分作品连载于报纸。已出版小说集《锅圈岩》,评论集《写作,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获第十届深圳青年文学奖。
(供图:徐畅 宫敏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