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传云资讯系统
中传云资讯系统华夏观察 | “双城记”的文化缠绕——评田粟《湾区梧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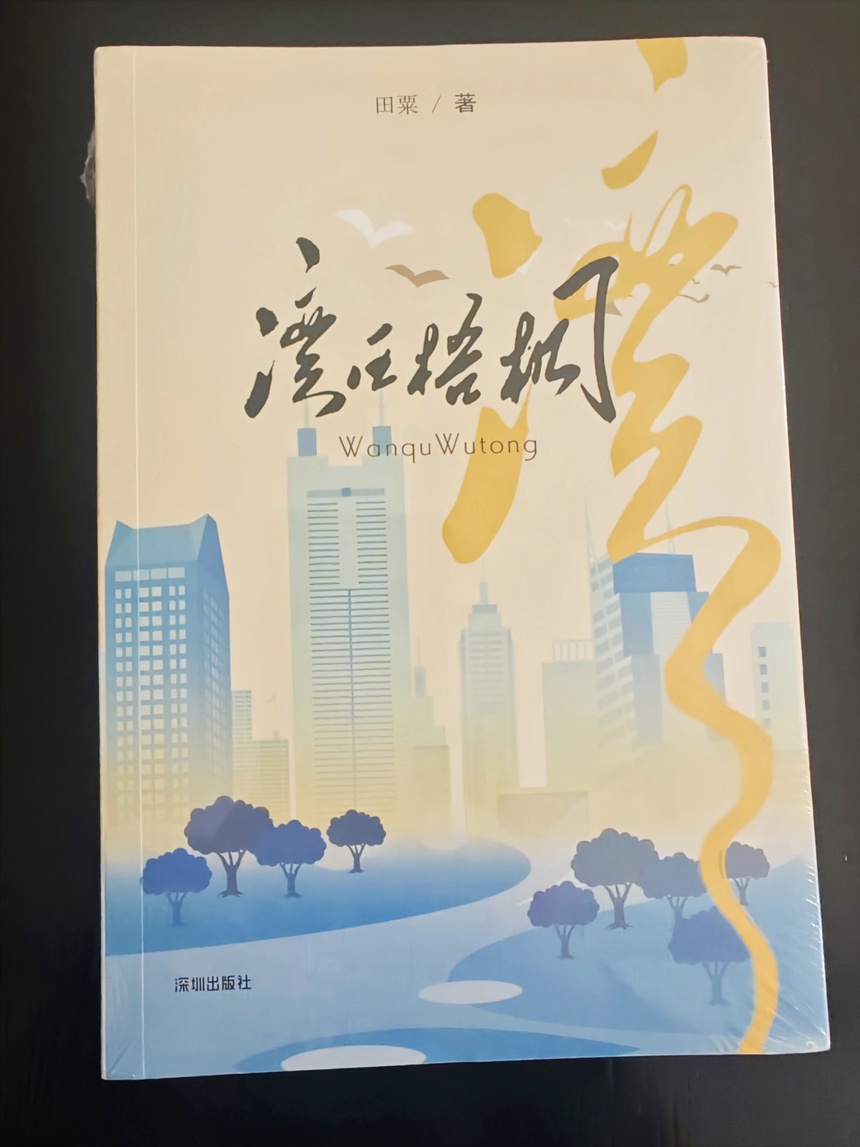
一向以写乡村和战争题材见长的小说家田粟此次把关切的目光聚焦到城市题材,出手不凡。长篇小说《湾区梧桐》是以深圳与香港两座城市的互动作为创作背景,牵涉到了双城人在事业与情感上的缠绕,这是一种“双城记”背后的文化缠绕,反射出历史的、当下的、文明的诸多问题。在田粟深具洞察力的叙述中,生气勃勃的深圳与香港的海关通道每天上演着经济来往与爱恨情仇,如此一来,深圳与香港在田粟的笔下,离得那么近,又那么远。
一座曾经繁华的旧城与一座正在奋起直追的新城之间,总存在着些许的矛盾,这矛盾被眼光锐利的小说家捕捉到。虽说小说作为社会研究的一种形式,但是田粟并没有成为政治作家,而是以婉转的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读者甚至发现作家田粟在小说叙事中自在地悠游,并能够意识到其中的某些不足,引导读者深思进而努力发现其前进的智识途径。
田粟作为一位长年工作在海关的作家,暗悉其中的奥秘,他能够把深圳与香港之间的故事讲得如此平易近人,如数家珍,但是却没有深陷,沉迷其中,他的虚构是一种艺术创造,更是一种人为的、简化的现实。小说中的深圳与香港似乎可以触手可及,但现实中的两座城市又隐而未见。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并不是直接地呈现城市面孔,而是在上面加了一个玻璃罩,如同卡尔维诺所说——“看不见的城市”。我们看见的深圳与香港并不是真正的深圳、香港。
深圳与香港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近些年来,更是有频繁的互动,必然会呈现它们背后更加复杂的东西。要深入深港两地的世界,要从它们之间的矛盾关系中发现秩序与规律,是作家田粟要奋力表现的地方,除去作家自身过多的自我感和历史感,而是把两座城市之间的文化缠绕解锁下来,条分缕析,深刻洞见文化与文明的冲突所带给普通人的命运安排。
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比较好的以深圳和香港为创作背景的是深圳作家吴君的小说《皇后大道》和蛰伏在深圳的导演白雪的电影《过春天》,他们都有书写这两座城市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笔下的主人公想尽全力从深圳到香港去。这两部作品都是一个当下的故事,可是故事的背后,折射的却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个时代留下的社会问题。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从深圳到香港去意味着一步登天,而田粟笔下的主人公陈熙怀在香港的生意破产后,是深圳敞开了温暖的怀抱收留了他,并让他东山再起。
通过这三部作品的比较,显然,深圳与香港的关系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尽管陈熙怀的太太刘琳在心理上并不认同深圳,而是执意留在香港,和自己的母亲一起生活,让儿子晋豪和爸爸生活在深圳,晋豪每天以通关的方式来香港读书,一家人分为两地的双城生活,这种社会现象,作为社会经济与历史的产物,生活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我们是非常熟悉的,它们代表了历史的某个阶段,或者代表了城市发展的某种阵痛。
留在香港的刘琳在情感上受到“港独”分子查理的欺骗,并险些丧命。
可是作家田粟却给了我们光明而温暖的结局,由港独势力策划的、有晋豪参加的粤港澳三地儿童画展爆炸案并没有发生,案发者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刘琳则是怀着万分愧疚的心情回归了家庭。小说的完美结局愈加突出了《湾区梧桐》中作家田粟的精神指向,虽说刘琳曾经有过迷失,但是她的迷失背后带出了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是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但是这两座城市构成了人们心中的某种向往,而这种向往又影响了每个人物的人生与命运的境况,这就是大时代之中的小人物的命运走向。
在全球一体化的动向中,《湾区梧桐》是田粟观察深圳与香港的繁盛与衰微中,为两座城市所作的空间比较的力作。比较的背后,是城市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为他者的比较。因此可以说,《湾区梧桐》以文化缠绕的方式向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空间视角。在这种空间视角下,“双城记”文化缠绕的关系如丝如缕,根系却始终扎根在一起。